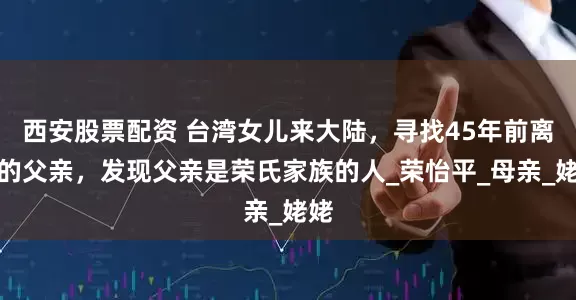
当然可以!我会保持每段的原意,丰富细节,同时尽量保持字数变化不大,给你改写如下:
---
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我在这头,大陆在那头。”
这句余光中当年写下的诗句,恰如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。那时通讯不发达,交通不便,多少人的思念都被这条浅浅的海峡阻隔在两岸,久久无法相聚,心中那份牵挂成为一生的挂念。
然而,也有那么一些人,不畏艰难,跨越层层高山和波涛汹涌的大海,执着追寻着内心深处的情感归属。在这其中,有欢笑与泪水,团聚的美满,也伴随着许多无奈和遗憾。
有一位执着的女孩,她一心寻找自己的父亲,怀揣着无法割舍的思念,跋山涉水多次去追寻那个虽未曾谋面却血脉相连的亲人。她从未被现实打倒,也无惧流言蜚语的侵扰。
这个不轻言放弃的女孩,花费了整整45年时间,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渴望的答案,重新拾回了遗失已久的亲情。
展开剩余91%荣怡平出生并成长于宝岛台湾,和许多台湾女孩一样,她说话柔和甜美,笑容温暖,总是轻声细语,显得斯文而乖巧。
但在这柔软的外表下,却隐藏着一股令人敬佩的坚韧和执着,她的灵魂中似乎蕴藏着与外表截然不同的刚强与坚定。
从小,荣怡平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勤奋和努力。她乖巧懂事,却对自己认定的目标异常坚持不懈。
这种韧性贯穿她的生活点滴。在家里,她年纪尚幼便开始帮助长辈分担家务,认真细致的态度常让照顾她的姥姥感到欣慰和骄傲。
进入学校后,她更是学习上的佼佼者,优异的成绩让她稳坐全校第一的宝座。“我从没拿过第二名。”荣怡平淡然一笑,却掩不住眼中的坚定。
当其他孩子还沉浸在玩耍和调皮时,她早已默默收起了孩童的天真。她清楚知道自己缺少什么,渴望得到什么。
母亲因工作繁忙,只有节假日才陪伴她,平时多由姥姥细心照料。家人都深爱着她,而她也非常懂事、听话。
自记事起,荣怡平便隐约感觉自己与其他孩子不同。虽然母亲和姥姥对她宠爱有加,但家中始终没有“爸爸”的身影。
幼时她曾试探性地询问过几次父亲的事情,却从未得到任何答复。虽然渴望知道,但面对家人的沉默,她也逐渐懂得不再追问。
常常,她会望着天空出神,在心底默默构筑那个未曾出现的父亲形象。
她对父亲一无所知——姓名、年龄、外貌、职业,甚至不知道他在母亲生命中的角色。
家中似乎默契地避开这个话题,父亲成为一个无人提及的禁忌。
五岁那年大年初二的晚上,一家人围坐欢聚,小表弟突然调皮地问:“我和其他小朋友都是和爸爸妈妈住,为什么你一直住在姥姥家?”
荣怡平愣住,心中五味杂陈,却装作轻松回答:“因为姥姥喜欢我,姥姥对我这么好,所以我才天天跟姥姥在一起。”
“哦,我知道了!小平姐姐没有爸爸,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吧!”表弟的天真无邪中带着刺痛的话语,令她心头一紧。
她强忍着眼泪,找借口回到房间,独自爆发出委屈的哭泣。
年幼的她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没有爸爸,为何与其他孩子不同,也不明白为何家人避而不谈。
这时,妈妈走进来,看到她泪眼婆娑,心疼地将她拥入怀中,母女二人紧紧相拥,泪水化作压抑已久的宣泄。
然而妈妈没有解释半句,只有悲伤的啜泣声伴随着她。
就在那一刻,五岁的荣怡平暗下决心,要变得足够优秀,成为最棒的那一个,这样才能不被别人轻视。
尽管不懂大人的故事,她隐约觉得自己是个“私生女”,妈妈的沉默也许是为了掩藏那段悲伤往事。
母亲在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。单身母亲带着无人解释父亲身份的孩子,常常遭受旁人异样眼光。
倔强的荣怡平只能更加努力学习,一次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,年年都是学校的模范生。她心疼母亲,母亲也为她骄傲。
但“爸爸是谁”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心头,挥之不去。
一个闷热潮湿的暑假,荣怡平在姨姥姥家无意中翻看一本旧相簿,细细辨认年轻时的家人们。
最后在散落的照片里,她发现了一张母亲与一位陌生男子的合影。
黑白照片上,母亲穿着洁白的旗袍,笑容灿烂又羞涩,头发插满绢花,披着轻纱。
男子身穿黑西装,发型整齐,英俊挺拔,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
荣怡平睁大眼睛,从未见过这个男人,但看着这张结婚照,心中隐隐明白了些什么。
她拿着照片找到姨姥姥,直截了当地问:“这是妈妈,那旁边是谁?”
这是家中避而不谈的秘密,被小小的她无意中揭开。
无奈之下,姨姥姥终于透露了父亲的名字和一些简略信息。
她知道了父亲叫荣郅隆,有根有名,不是无根的野孩子,也不是被迫诞生的私生女。
虽然细节寥寥,荣怡平仍从零碎中拼凑出部分真相。
父母曾在台湾结婚,生活和睦相敬如宾。
时代背景让他们难以回大陆探亲,思乡之情浓重却难以团聚。
母亲怀孕后夫妻二人满怀喜悦,期待着三口之家生活。
然而某天,父亲突然消失,没有任何预兆,也未留下只言片语,彻底失去了踪影。
母亲四处寻找,眼看临盆,却无处寻得丈夫的踪迹。
她猜测父亲可能偷偷回大陆探亲,但放弃了孕妻和腹中胎儿,这是无法原谅的背叛。
从那以后,母亲对父亲满怀恨意。
荣怡平虽然不懂父亲为何离去,却从小就能体会母亲的痛恨,但她自己并无怨恨之心。
她内心渴望父爱,不愿责怪父亲。
明白母亲闭口不谈是为了不再唤起痛苦,荣怡平在心底埋下种子:“总有一天,我要去大陆寻找父亲。”
25岁那年,她首次踏上大陆,怀着仅有的名字、籍贯和大致生日,开始寻父之旅。
在十几亿人口中找寻失踪二十多年的亲人,几乎如大海捞针,充满无力感。
本无太大期望,她随意打听,却在上海图书馆意外发现了父亲家族的族谱。
那天,正当准备返程,图书馆里满是陈旧纸张与油墨的味道,她偶然翻到一册“荣氏族谱”,发现了“郅隆”二字,心跳加速。
她复印下来,带回台湾,虽然线索有限,却坚信这是成功的开端。
回台后,因无头绪,暂时搁置寻找计划。她过上平静生活,结婚生子。
怀孕时,她终于理解了母亲的心情。
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,那个最该陪伴的男人却突然消失,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。
身为母亲,她能共情母亲的怨恨,却依然不怪父亲。
许多人认为父亲抛妻弃女不可原谅,但荣怡平觉得“每个人都有难以言说的苦衷”,也许父亲是怕见了女儿后再也舍不得离开。
多年奔波却无突破。
45岁时,她再次踏上大陆寻父之路,这次带上了母亲。
起初母亲不愿,但母女情深,荣怡平是妈妈的骄傲,妈妈也愿为她放下多年怨恨。
终于,她们在父亲的故乡找到了亲人!
见到未曾谋面的堂姐,血缘的亲切感让她们紧紧拥抱。
然而,堂姐泪眼婆娑带来了噩耗:父亲荣郅隆于1979年1月28日因病去世,至今已逾三十载。
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,荣怡平呆立原地,泪水夺眶而出。
虽然早有最坏打算,却从未想过真相竟是如此痛苦:“那时候我才8岁!”她哭得肝肠寸断。
她不知道父亲是否幸福,有无再婚,但怎料他竟未曾享受过人生的幸福,英年早逝。
堂姐拿出父亲的单人照:荣郅隆仪表堂堂,西装革履,神采飞扬,微笑面对镜头。
荣怡平反复触摸照片,感叹“我的耳朵和爸爸一模一样”,泪流满面。
堂姐告诉她,父亲未再婚,他当年离开是为了回大陆见母亲最后一面。
信息闭塞年代,联系困难,他不得不离开。
可惜母亲已早逝,父亲未能
发布于:天津市粤友钱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